讲座|倪剑青&郁喆隽:人人都是犬儒主义者?
原标题:讲座|倪剑青&郁喆隽:人人都是犬儒主义者?
英国学者安斯加尔·艾伦(Ansgar Allen)的《犬儒主义》,从大众的视角出发,介绍了犬儒主义这种思潮从古至今的演变,也反思了犬儒主义在当代社会当中扮演的角色。该书的中文版近日由风之回响工作室以及合作伙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联合推出。4月1日,出版方邀请了中文版译者、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倪剑青,以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郁喆隽,举办了一场新书分享会。活动由《犬儒主义》的编辑顾霄容主持。本文为此次分享会中嘉宾的部分发言整理,经审定发表。

讲座现场
顾霄容:今天活动的主题是“人人都是犬儒主义者?”,这句话是有出处的,它出自书的第三页:“现代犬儒主义已经融入了社会主流,再也不是只有社会少数派才会皈依并践行的一种哲学——我们现在都是现代犬儒主义者”,在第七页也有类似的表述:“毫不意外,我们都有自己的犬儒时刻”……我给这本书写的文案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明知是毫无意义之事,何以还会一面嘲讽一面执行。”虽然这句话很可惜后来没用上,但其实它就是针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种现代犬儒主义的现象。对于这一面,倪老师在中译本序言里也写过类似的表述,倪老师说:“在匿名化的社交媒体上冷嘲热讽,在真人出场的现实场景中唯唯诺诺”,从中就可以看到现代犬儒主义是在顺从的同时还带着一肚子的不满。但同时这本书里面也有大量的地方讲到现代犬儒主义还有反叛的一面,但是顺从和反叛之间其实存在一种张力。那么两位嘉宾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呢?
倪剑青:我之前也在一段文字稿中写过我对这本书的整体看法,即“什么叫犬儒主义”?不管这位Allen仁兄用了大小写区分,还是像一个德国人用了K和C开头区分,古代犬儒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不管怎样,只要它叫犬儒主义,就是用了同一个词或者同一个声音,我们总是觉得在这当中是有一些共同之处的。我觉得要先说一下共同之处,之后我们有可能才明白犬儒主义的反抗和顺从到底是什么。
整体上,犬儒主义有两个核心特质。第一个特质是他们自以为把握真理。刚才我的一位朋友跟我说这本书对当代的情况评价是全局性的,在这位作者的眼中,所有人都是犬儒主义者,我觉得其实并不是。犬儒主义有两个核心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把握真理,且这个真理不是自然科学真理,而是人际关系上的真相。人际关系包括了办公室、家庭,以及人和人组成的形形色色的组织,家庭、社会、俱乐部、国家等等。只要你认为当中有某种“真”被你把握到了,不管你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权力之间的关系或者别的什么,你就符合了条件一,即你把握了真理。条件二是你看不上人类且包括自己。即你在知道真理之后,不会为真理做任何事情。因为人类已经在污泥之中了,人类不会有任何的改进。获得真理跟做出改进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真理只是让你获得了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你会更加明白人类是无可救药的,现实是不可改变的,因此你就躺下来了,失去了任何行动能力。在这点上你非但要鄙视大部分人,还要鄙视自己。因为你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否则你就不应该活在这里。城邦之外非神即兽,你应该离开城邦去变成一个神一般的赫拉克里特似的人物,或者说变成一个野兽似的人物,像施洗约翰这样的人,而不应该作为任何一个城邦的公民而存在。因为你会发现,人类的平庸性,或者说卑下状态在各个地方都存在,这是条件二。
综上,第一个条件是得把握人际真理,第二个条件是得看不起人类包括自己。只有两个条件并在一起,你才变成现代犬儒。古代犬儒主义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第欧根尼进行表演的时候,你觉得他真得会认为这样的表演很好吗?你去问第欧根尼,如果他愿意回答的话,他会告诉你,不得已而已。如果他活在一个他想象的理想社会当中,他不应该当场脱下裤子放屁拉屎,这样的行为至少不是正派的。而正因为他活在一个人类处于非常糟糕的堕落状态下,他只能通过这样深具刺激性、冒犯性的方式来刺痛你,就像苏格拉底化身为牛虻去刺激雅典人一样。这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堕落了,并且他也是堕落者一部分。既然他视他们为同胞,所以他也是堕落者。
所以在这点上,我们回到一开始顾老师问的关于反抗和顺从的问题。我不想说什么辩证法。在我看来,只要你愿意活在某一个群体里,不管这个群体是叫家庭还是叫社会,还是某个具体的国家,只要你不采取一种出走或者类似的极端行为,只要你还在里面参与了某些工作,而这些工作你认为是对其他人有利的,不论是通过键盘来发言,还是从事实际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顺从。顺从是第一位的,顺从标志着我们是处于一个非自愿的、被统治的状态。我们当然可以选择逃避统治的艺术,但是不论你是逃避统治也罢,还是甘心请愿被统治也罢,在我看起来都有顺从的部分。你有了顺从,就会感到不满,这个不满因为你不是个物而是个人,那么你就会有一些反抗,但是最终你还是选择顺从。为什么?因为人毕竟是要吃饭的,人必须要活下去,人必须完成自身的及其后代的再生产等等。
郁喆隽:倪老师一紧张讲话就会比较快一点,其实在短暂的几分钟里面给出了很多密集的知识点,这大概是一个大学老师的职业病。但是当我听到前面一半倪老师列出了犬儒主义两个特征时,突然就感受到倪老师已经成功研发出犬儒主义的一个“抗原测试”,自测一下就能马上知道。
当然,他后面的话引出我更多的问题。一个很大的个人困惑,或者说我们自己读这样的书的时候,都不由自主会对号入座去想,我自己的处境大概是什么样子。其实这就是刚刚顾霄容提的问题,反抗跟顺从之间,犬儒主义一开始的界定就给人有一种勇气不足所以不足以起来反抗的感觉。但另外一方面也暗示,恰恰是因为勇气不足,给现存的秩序或制度安排再添一个燃料,使得秩序或制度安排更加稳固,辖制力会更强一点,这是我个人的代入的想法。当然,倪老师刚刚给出了一个近乎是生物学的解释。
我们有一些最基本的底层需求、欲念需要去完成,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恰恰是苏格拉底给我们指出来的另外一条道路,其实我们是因为缺乏认识,因为无知,而导致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到底是因为无知还是因为无能导致了这种犬儒主义?
有的时候我认为可能大部分人还是处于一种不是无能而是无知的状态。当然,这也取决于大家对不仅是哲学史(的认知)。哲学史其实是我们当下人的一个生活状态,面对比如像苏格拉底这样在公元前399年被雅典判处死刑之后的不同学派的一种反应,到底应该逃还是不逃?即倪老师刚刚问的,我们逃离城邦去做神、做兽?还是继续回到城邦里面去尝试改变洞穴当中的一些幻象,把洞穴里面继续沉睡或者影影绰绰的影子唤醒?
这大概是我代入思考的问题,但其实会引发出对传统主义核心的定义。定义大概是很容易可以发现的,但光有“抗原测试”是不够的,后面有个病例存在。为什么我们会得这种病,以及我们更关心的是接下来的问题即这种病有没有方法医治。
倪剑青:不好意思,我又陷入了我上课时比较容易陷入的状态。刚才我就是在思考郁老师提出的问题以及我前面的回应。我想进行一些修正或补充。第一点就是犬儒主义的第一个特质是自以为把握真理,在这里我要做一个更加细致的区分。
第一个区分是关于真理的态度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感到自豪,是因为我们把握真理这件事情而感到自豪,还是为真理本身而感到自豪。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对真理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追求真理,但并不因为我们获得真理而感到自豪,而是因为真理本身而自豪。如果我们因为自己获得真理而感到自豪,沾沾自喜:“我把握了真理,真理具有我的某些特质,因此我跟真理在一起了”,简直就像路上一条狗看到一根电线杆,去撒了泡尿,就自以为这根电线杆是它的了。如果是这个情况,你就有可能是个犬儒主义者,因为你对真理的本质不关心,本质上是关心你自己。
第二个区分是要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顺从和反抗。我经常说犬儒主义很特别的一点在于,它有点像网上的喷子。假设出了一个新游戏,有些人会很享受它,关卡自己打不过去就去看看云游戏,看别人怎么打过去,最后也很开心;而有些人则热衷于对这个游戏进行冷嘲热讽。自己实际游戏时间很短,但是可以输出一大堆批评。批评完了,游戏热度过去了,就换一个游戏批评,永远处于一种批评状态,这种人会在这个批评状态当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满足感,自以为我是多么的厉害,对什么东西都能说两句,对游戏甚至游戏本身的游戏性都有个深切的把握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犬儒主义的反抗本质上是犬儒主义者根本不认为有一种能够得到完满的人类处境。一种理想的、善的状态,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因此犬儒主义者在任何一个建制或任何一个体制下面,都会采取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反抗是为了什么?犬儒主义者的反抗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或者办公室中的不满是为了建立起一个更好的职场?不,犬儒主义者不追求这些。犬儒主义者追求保持一种冷嘲热讽的、超然的态度,就是在这种态度当中,他获得了最大快感。所以,我说犬儒主义者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生。
最后就是郁老师问的问题,犬儒主义者到底是无能还是无知?我觉得对于古代犬儒主义者来说,他们不是无能也不是无知。他们是正儿八经的哲学家,他们有着对当时而言极佳的哲学训练。同样,他们也不无能。当代一个人要是去干这些事情的话,那他就被称作行为艺术家。我对行为艺术家历来是很佩服的,他们能够以自己作为一个艺术的装置,放在公众面前——别说艺术装置,我社交焦虑,在这里就如坐针毡。对现代犬儒主义者来说,我觉得他们也不是无能,也不是无知。他们是我前面说的态度问题。什么叫态度问题?我不知道下面的说法对于诸位来说是不是好理解。有种态度我们称为“就事论事”。如果别人来问你道数学题、问对这本书的看法,或因为纯粹不知道而问你历史上发生的某件事件大概是什么样子,你能就事论事地说,暂时撇开个人的立场好恶,单纯地把知道的知识传达给别人,那么你就拥有一种特殊能力。,这种能力我们叫做语义层面上的能力,大白话就是一种就事论事的能力。但是如果你想在里面贩卖私货,不管你的私货是什么,给别人安利某些东西、表达自己愤怒,或者显示自己博学多才等等,这种情况下你就有可能进入了犬儒主义的行列中。也就是说,他们自认为掌握真理,但他们有可能是离真理最远的,他们无法做到“就事论事”的态度。这决定了他们无法享受真正的“真”。
郁喆隽:其实大家一定要很小心,因为他作为译者对这个书是比较熟悉的。刚才简短的一段回答,前面一段是在讲当代犬儒主义,后面就在讲古代的犬儒主义,倪老师自己是很清楚和容易区分的,而我把这本书读完了也相对知道在讲两个通用的同一个犬儒主义。但其实存在一个古今颠倒、错位的角色,现代犬儒是一个经过现代慢慢的消化、借壳上市的犬儒主义,是我们大部分人痛恨的,需要我们做自我诊断的犬儒主义,包括倪老师前面提出的两个标准,其实是现代犬儒主义的标准。我们每个人暗戳戳躲在键盘后面,在社交媒体上做出一种大义凛然的姿态,反复登上道德的制高点,对别人进行持续的批评,但自己又始终保持置身事外的状态,显然是一种现代犬儒主义。
这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两者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倪老师刚才其实点出了一个关键词,也是我也一直在想的问题,即古代的犬儒主义实际上并非我们现在的学院派,不是哲学家,也不是老师,而是像行为艺术家。因为古代犬儒主义者的某些行为,显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蓄意为之。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现在大部分的哲学老师也好,工作者也好,主要的劳动工具是语言,但古代哲学家的劳动工具也可以是行为,即所谓的言传身教。我的一个体会是,某种程度上,对于古代犬儒主义者来说,他们是“哀莫大于心不死”的一类人。我们汉语里面通常讲的是哀莫大于心死,索性心死一走了之,或者说用更激进的方式来反抗,但是古代犬儒主义者是典型的“哀莫大于心不死”,即他不认同现有的社会规范制度,所谓的风俗,但他又用另外一种接近于行为艺术的方式去冷嘲热讽——只在冷嘲热讽这一点上,古代犬儒主义跟现在犬儒主义是高度相似的。但是倪老师刚才讲的一个态度问题,犬儒主义的冷嘲热讽还是有所求的,目的要达成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很可能是委婉、曲折的。所以我说哀莫大于心不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比如说第欧根尼像狗一样的生活,犬儒主义者为什么一定要在木桶里面,在广场边上,为什么不能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像狗一样地生活,我记得这本书在后半段有一句话是后世的人对第欧根尼的评价:第欧根尼什么都不缺,他只缺一群观众。那么当我们不去做神、不去做兽的时候,当我们还在城邦当中需要有一群观众的时候,其实还是哀莫大于心不死,还是想通过自己的行为能够有所改变。但怎么实现改变?反讽也好,嘲笑也好,这是一个很曲折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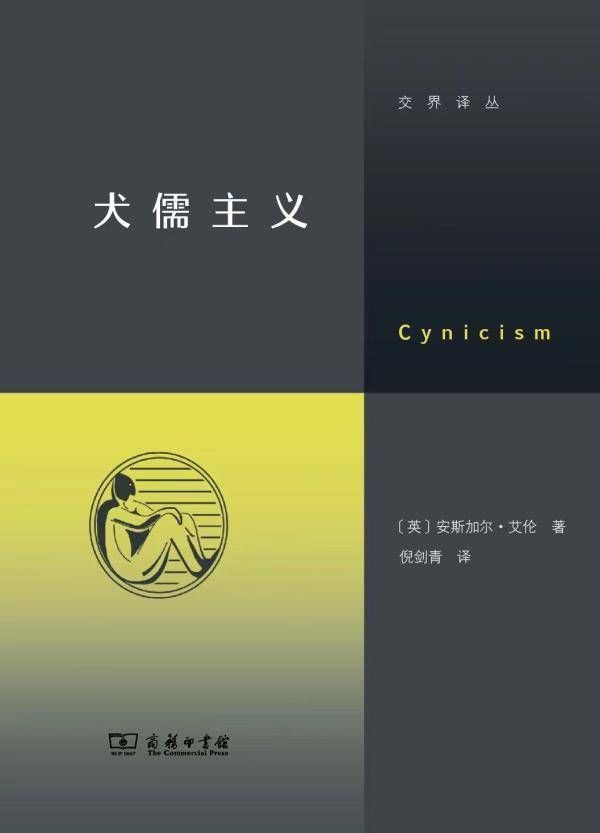
《犬儒主义》,商务印书馆,2023年3月版
顾霄容:从刚刚两位嘉宾的发言当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古代犬儒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虽然共用了“犬儒主义”这个名称,但两者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截然相反。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从古代犬儒主义到现代犬儒主义,中间经过从希腊化时代到早期现代,如此多的哲学家也好,思想家也好,两种犬儒主义之所以能够共享这个名称,是离不开这样一群人的,离不开他们的挪用和改写。就这本书里面讲到的多次的挪用和改写,对于两位嘉宾来说,哪一次的挪用和改写是让您印象最为深刻,或者让您觉得最值得注意的?
倪剑青:我再澄清一下我前面的一个说法。我前面指的两个标准是我认为古代犬儒主义和现代犬儒主义共同通用的。至于说这两者之间差别到底在哪里,一定要指出来的话,在我看来,古代犬儒主义的目的是唤醒大众,具有公共性,它是面向公共领域的。在希腊人的生活当中,一直是有公共领域的,比如广场。所以第欧根尼会住在广场边,他始终是为了他人的。而现代犬儒主义者从来不在广场上。因为如果他在广场上,他就成为了革命者,而不是犬儒主义者。现代犬儒主义者只会在阴暗的半地下室,有电脑显示屏的反光,墙上挂幅世界地图,地图上还有红蓝铅笔画出的各种各样的进攻路线。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犬儒心态才有可能起效。
至于你说的挪用,我偏向于认为这本书论述从古代犬儒主义到现代犬儒主义的转变不是特别地清楚。因为的确也没有一个清楚的关节点可以反映出存在一个决定性人物,在他身上既可以看到古代犬儒主义的影子,又可以看到现代的影子。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从古代后期对所谓街头犬儒的持续打压,以及把非街头的哲学家犬儒经典化,进一步到中世纪时公众对暴民的恐惧,认为必须要维持一个基督教世界的最基本秩序,然后到近代早期出现了对那种不尊重人性、压抑人性的旧制度,包括封建等级制度和教阶制度的反抗。因此,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种种文学作品当中,一方面是出现了很多的虚伪者,另一方面是出现一些完全以自己肉身的欲望或者说快感为追求的人。虚伪者毫无疑问,在《十日谈》或者各种各样的同时代作品当中看到神父型的形象,主要是教阶制度中的教士。他们一边嘴上说着神与道德,事实上则男盗女娼。大家对此都有所知悉。还有就是一个完全以身体快感为旨归的生活方式,书中以拉伯雷的《巨人传》为例。《巨人传》是非常典型的,对现代人来说难以想象,为什么当时会喜欢这样一种高度戏谑化、高度以身体为中心的叙事?进一步地,包括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薄伽丘的《十日谈》都是高度以身体快感为中心的戏谑化的叙事。后来我才渐渐意识到从古代犬儒主义到现代犬儒主义的这种转折有可能是很大尺度的,因此难以被准确观察到。人们开始意识到传统秩序的问题,个人对它有很多的讽刺、不满、反抗,但是最终无法去真正消灭秩序。在我们这里的语境中,这个秩序是中世纪晚期弥散在欧洲的基督教的教权-王权体系。普通人无法去反抗它。而且那时每个人的生命也朝不保夕,人们能够追求的无非就是个人微小的快感生活,连幸福生活都称不上。因为幸福生活要求是很高的。诸位当中有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古代希腊人对幸福的要求很高。首先是要身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还需要有运气,要欣赏人生的哲学智慧,而且幸福必须要持续整个人生。这个要求太高了,我们能够追求的无非是《十日谈》或者拉伯雷的《巨人传》里面出现的身体式快感。不论快感来自于食欲、性欲或者别的什么欲望,对现代人而言,这些东西才能真正追求。
所以在我看起来《拉摩的侄儿》当中出现的“侄儿”就是第一个完全以现代面目出现的犬儒主义者。明明某些事情很糟糕,我自己却没法反抗它,甚至需要参与当中分享这件事情的现实利益,需要伪装成大家能够接受的面目。必须把怨恨、不满放在心里,然后才有资格能去分赃。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又咬牙切齿地对他们表示不屑,也对那个与他们同流合污的自己表示不屑。
这点上我觉得这提示出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从中世纪晚期的以身体快感为中心的叙事转向《拉摩的侄儿》,那种我无法改变的深切无力感。我所追求的无非是我的快感,而我的快感来源又被垄断。这点很有意思,艾伦这本书里面因此谈到了萨德。当然我们这里不能多谈萨德,我对萨德也不熟悉。但很明显的一点是,我们的快感来源被垄断了,快感来源不能是我们自己。古代希腊人的快感来源有可能是他们自己,也有可能是他们的同伴,总体上这是他们自己可控的。到了统治或者体制变得无比巨大的时候,快感来源完全被垄断。比方说现在诸位有可能晚上回去要刷刷剧,那么剧的来源在哪里?B站、抖音等各种各样的内容平台。当然也可以通过某种盗版的方式获取。然后是各种各样的物质,酒精、饮料等等。这也都是被垄断了的,都是不在你掌控之中的。正因为别人掌控了你的快感来源,所以你才需要跟他们合作,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快感,所以在实现过程当中,你只能咬牙切齿。你除了让自己的身体绑定快感之外,别无所求。那种宏大的叙事,高远的理想,或者那种激动人心的东西,已经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了。我们拥有的东西其实都已经被别人掌控住了。所以才会有一种弥散性的怨恨。在我看起来正因为有怨恨,才会有一种暗地里的咬牙切齿和表面上的卑躬屈膝的结合。
郁喆隽:我觉得倪老师讲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我就接着他的话往下来讲。
其实我的理解是本质上犬儒主义者是一个戒断多巴胺的失败者。网上现在有很多方法,以一种非常超脱的但实际跟消费主义高度同盟的方式戒断多巴胺。就如刚刚倪老师所说,快感来源被垄断很像犬儒主义者的一个核心特征,犬儒主义者本身要对这个社会现有的风俗习惯提出质疑或挑战,反讽或者嘲笑的最大用意在于对这种虚伪本身提出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他提出问号的方式本身也是极度虚伪、言行不一、表里不合的。当然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稍后可以来讨论,即犬儒主义不从哲学角度反而从戏剧理论的角度来讨论,从犬儒主义者第一人称直观的角度来说他有没有表演技术。
回到刚才多巴胺戒断失败的一种表现的话题,我们现代大部分人可能都是如此,已经对某些东西有一种强烈的依赖感,但是又没有办法彻底戒断它,所以不得不用一种戒断失败的方式去挑战它。本身行为上是有一种背叛,但又要获得某种他所允许的这种快感,要暗戳戳地进行某种冷嘲热讽的时候,似乎是没有办法想彻底戒断之后会是怎样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造成古代犬儒主义与现代犬儒主义形成180度倒转的核心问题。因为从我们哲学史或者思想的角度来说,希腊人的一个核心理想是人是自给自足的,或者至少是自洽的,但对于我们现在的人,不管启蒙运动的那些人如何说你们可以做一个顶天立地、自作主张的一个人,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包括消费、生产方式、社会的组织结构,都使得我们其实是处于一个高度矛盾的状态,即观念上我们想要做到顶天立地、自作主张,但实际上我们方方面面、千丝万缕的事物,包括肉身也好,最底层的屎尿屁也好,都是高度依赖别人的。简单来说,我们其实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对外部世界包括对别人的依赖。外部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我们很难真正像古代犬儒者那么决绝地表达不满。我们所有的表达都是有所保留的,我们不可能那么的彻底,而倪老师刚刚讲的那些当代在网络上表现出来的好像很决绝、很激进的表达,实际上也都是处于一个舒适区内,在一个非常心知肚明的安全区当中。所以我觉得现代犬儒主义者不自知的表演性就是因此而产生的。
倪剑青:因为我在思考郁老师提出的问题,所以我先回答我能够记起来的东西。
第一个是关于表演性。第一人称角度来看存在表演性。在我看起来这当然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就像现在我都意识到自己有一些做法可能存在表演性。我在讲台上有时候也非常具有表演性,有些言辞和行为明显是因为讲台效果而做出来的。反过来推,由此及彼,由己及人,我相信犬儒主义者也会有高度表演性,只不过他把控得好,知道自己表演应该在哪里终止,知道自己表演是为了达成什么样的目的。他们掌控一切。-这本书里面就有个词叫“self-master”,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我翻译成“自我掌控”。大家知道“master”一词的意思,主人、大师、掌控者。因为“self-master”这个词中主要是强调动词性的“master”,因此是自己掌控自己。我觉得这个短语是很难翻译成别的词的,因此这个短语其核心就是自己掌控自己的意思。“掌控自己”,这是古代人的一个理想,也是古代犬儒主义的一个理想。要掌控自己生活和行为的方方面面,那么在这个掌控当中,他会具有表演性质。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他完全自我掌控了,哪怕他可能什么都不做,当他跟他人在一起时,那种自我掌控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转换为掌控你给他人留下的印象。我们大家有可能在职场上常见到这样的人,他会很好地控制自己,他会留下一个他想给你留下的印象。在这点上,他是个高度自控的人,远比我们这种一触即跳、很容易被人煽动的人好很多。我们称不上自由自在。
第二个,我认为古代犬儒主义和现在犬儒主义可能都有一个核心的毛病,这也是我回应前面我的一位朋友说的,是不是所有人都是犬儒主义者,这样的问题。犬儒主义有个很明显的特质,即它存在某种想象力的匮乏。也就是说,他不能想象出与当下世界不同的未来世界,他对未来世界的想象,跟现在的世界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来看古代犬儒主义,假设第欧根尼他赢了,不管是哪种意义上赢了,让他来系统地改造雅典,你认为他系统改造过的雅典是一个什么样的雅典?人人赤身裸体,像狗一样在马路上到处拉屎拉尿的雅典?当然不是这样的雅典。第欧根尼能想象改造出来的雅典不会与当时的雅典有什么大的区别,最多每个人都变成了正人君子。就像刚刚郁喆隽老师说的,每个人都处于一个君子国当中,满街都是圣人。只不过每个圣人成色不太一样,有些是一吨重的圣人,有些是50克的圣人。那么现代犬儒主义的这种毛病就更明确了。不要说现代犬儒主义了,就比如当代网上的键盘侠就深陷这种想象力匮乏的病症中。这里,我要承认我就曾是个键盘侠,只不过没有赶上社交媒体传播的时代而已。我曾每天花8个小时在网上与网友奋战,甚至彼此约过架,尽管别人放了我鸽子。如果你问那时候充满愤怒的我,甚至你问现在的我,能想象一个跟现在不一样的未来社会吗?或者假设你有这样的能力,不管是权力也罢,许愿瓶也罢,放出一个瓶子里的妖怪也罢,让你想象有机会塑造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或者有机会去掌控未来,你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你设想的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我承认,我是想不出任何一个不一样的未来。这点上我和郁老师都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培养出来的。哲学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师一直说,马克思是能够设想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的人。此外,传统的基督宗教也能设想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那些未来想象是否具有可行性不重要,设想未来不需要提供可行性,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选择。安斯加·艾伦在这本书当中也说道,另一个世界,另一种可能性,别样的社会。这是现代犬儒主义者想象不出来的。他只能想象出来一个当下的加强版,这个加强版有可能是往这个方向加强,有可能往别的方向加强,有可能是一个青春版、乞丐版、旗舰版、尊享版……不论怎样,都是对当下世界的加加减减与变形。他不能想象出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样子。哪怕我现在告诉你们,从明天开始资本主义原则被废除了,大家要根据心中的爱,根据爱的不同程度来划分社会等级,你能想象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吗?我完全想象不出来。
那么同样的,我们回过头来说,正因为我们想象不出未来,所以我们才把所有的未来视为当下的某种变形。我们没有未来,我们只有形形色色的当下。其实当下是并列的,以空间的形式彼此并列在我们面前。因此我们对它进行各种各样的冷嘲热讽,试图拉开与它的距离,试图把自己摘出去。但是我们又知道没办法摘出去,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一种别样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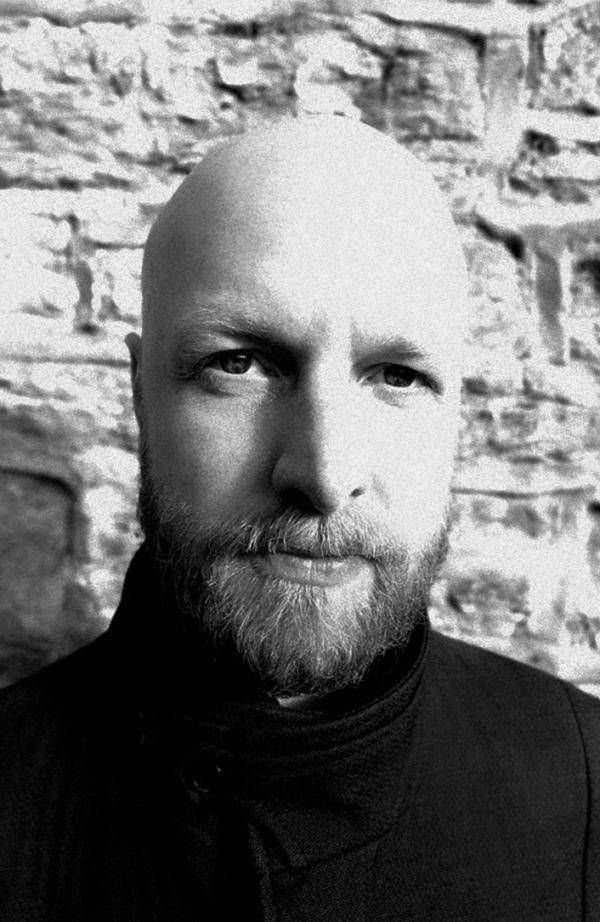
安斯加尔·艾伦
顾霄容: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倪老师在这本书的序言里面也讲到这本书的作者安斯加尔·艾伦主要研究领域是教育哲学,两位嘉宾作为大学老师,同时在家里面也是家长、长辈,在双重身份的背景下面,两位是如何看待艾伦笔下的犬儒主义和教育的关系?以及书中的这些描述,对两位日常的教学和教育有什么启示吗?
倪剑青:对于我自己家里的教育,我谈不出什么。因为我的孩子刚出生不久,所以还谈不上教育不教育,现在只希望他能够顺利长大而已。我和郁老师都是高校老师,而且郁老师入职时间比较长,我毕业时间比较晚——也都入职超过10年了——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根据这些想法,关于教育是现代犬儒主义最深重的地方这个观点,我觉得是挺正确的。
当代中国的高校教育有很多问题,其中有些问题大家也都知道。但这里还存在着一个代际的差异。对我们的本科时代而言,教育的问题展示在“颓废”上。在高中阶段辛辛苦苦读书,然后在大学阶段放飞自我,什么都不干,整个人都颓废下去,甚至还会比谁比谁更颓废——颓废是一种文学青年的象征。但当下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我们面对的本科生,则有可能完全不一样。有些人受到的教育非常好,明显超过了我和郁老师这代人受到的高中教育水平,但他们有他们的问题。比如说同学当中有一些人从非常严酷的应试教育筛选中奔赴过来,他们的确是高考的胜利者,但是他们一旦在大学当中,有可能会适应不良——并不是说他们学不了,而是说他们会深深地感到自卑。也就是说,别人知道的东西他不知道,别人享受过的东西他没享受过。他之前辛辛苦苦地在小镇做题爬到了这里,但觉得全面地比不上大城市的普通孩子。再比如说,我也是进了现在的大学任教才知道,学生开始实习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早,甚至有从大一就开始实习的例子,这让人非常震惊。还有,我们的大学教育现在高不成、低不就。自诩为教育家的人往往说我们的大学是学术型的大学或研究型的大学,继承了威廉·冯·洪堡的理想,但是事实上我们做到的无非是高等职业教育,而且这种高等职业教育做得还不够好。很多本科生说上课学的东西在职场上完全没用,要去实习的时候还是需要别人手把手地从头开始教。我当时就问他们,要不要考虑一下这样的一个方式:“比方说进了我们这个大学,从大一开始就实习,你们先别上课,先实习两年再回来上课。”他们说也不行,课堂上教的东西尽管对具体的东西没用,但是如果不学,对所从事的行当到底在做什么以及未来职业发展的整体途径无法把握。这导致现在的情况很尴尬。一方面本科生要比一般的职业高中或职业教育的学生在理论知识上更好,但是具体实操上却比不过对方。本科生好像接受了一些理论教育,但是大学时代的理论教育肯定是不够的,甚至是没用的。在职场上,你做得最多的事情是什么?大家作为本科生毕业之后,大部分时间在做什么?在操作Excel。不管你那时候学的是Python还是什么,最后你还是跟Excel打交道。这个情况提示了现在学校教育遇到的一个巨大问题。那么你怎么来衡量教育的好坏?从学生、从学校、从家长看来,这其实很简单。第一,应届毕业生去找工作,对学校而言,就业率是多少?对学生和家长来说,工作赚了多少钱?第二,一门课程的优良率或优秀率是有一定限制的,无非是通过这些来给人排序。我当然能够理解人群总是呈正态分布的,但是学校强行给出这样的限制,就会导致学生为了追求一个更好的分数而变得特别卷,所有的学习最终是为了一个分数,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东西。
一旦谈到教育,我可能就会关注一些很实际的现象,就不会理论地去谈。我觉得尤其心痛的是,有些孩子我觉得是蛮有天分的,但最后却是走上职场的道路,泯然众人。也许我觉得他们去做学术会更好一点,会活得更自在、更自由一点。
郁喆隽:倪老师讲的我也是感同身受,但是我换一个说法。我最近在想一些问题,我这个学期开了门荣誉课,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仪式是什么回事,ritual或者叫rite,这是宗教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我问了很多同学一个问题,我们在大学里上课都是正襟危坐,所有的学生现在每人一台笔记本,好像在做笔记的样子,但说不定他在看别的网站,或者购物,或者在发抖音,然后一个穿着比较体面的大学老师在讲台上手舞足蹈、声情并茂地讲一些他想讲的内容,我就问学生们这个上课现场,它是不是个仪式?然后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一个更要命的问题,像他这样一种上课的现场、这种行为和一场cosplay有什么区别?有没有可能坐在现场的人,包括讲课的人,都是虚情假意,在完成一个规定动作,一个标准动作?其实这也是我自己当老师的年数渐长,会产生的一种强烈的虚无主义、犬儒主义时刻。什么意思?因为当老师的一个基本前提、职业伦理,即认为人是可教的,但是跟老师接触时间多了之后,包括跟同行的大学老师,越来越会发现,实际上的大学老师轻易地、不知不觉地滑向了职业信念、职业伦理的对立面,就从相信“人是可教的”转向了“人是不可教的”。而且所有发生都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自己不自知的情况下,就会发现现在的大学更像是一个工厂,像流水线,你的上游给你的来料,你要加工的这个人,他可能已经变得不那么好教了,因为有大量的东西已经在他脑子里了。
众所周知,人是一种奇怪的生物,人是为了捍卫自己的错误信念可以跟你拼命的生物,而且付出高昂的代价捍卫自己的错误的人会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此,有很多类似的事情会让我们自己觉得慢慢陷入了一种圈。那么我面对这些不可教的人,我还要教他,应该怎么办?无非是往两个可能性发展:一个可能性就是自己越来越犬儒主义了,虽“不可教”但我还是要装模作样地教一下;另一个可能性就是触底反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不是像大部分犬儒主义者那样知其可为而不为。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大学老师可能都会有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大学教育像一场一场集体的、盛大的cosplay,大家都装模作样,上课装模作样,考试装模作样,给分装模作样,最后装模作样毕业。至于学生获得了什么,好像也不是很清楚,最后当然获得了一个文凭、一个绩点,但也变成了学生继续去卷的一个起点。
倪剑青:郁老师这点说得很对。我前面还在想,大学教育和中等教育有可能不太一样,安斯加尔·艾伦说的是中等教育,给学生以极大的挫败感。我们读书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比较宽松,而像现在某些高考机器型学校,有可能给学生极大的挫败感,然后把学生整个人都塑造成了应试教育的形状,这些人到了大学里面有可能会遇到严重挫折。我的妻子是北大毕业的,她所在的心理学专业,一直在北大和清华做一些跟学校相关的心理方面的调查。她告诉我,有一个现象在北大、清华特别明显,来到复旦任教以后自己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如果你(大学生)是高考机器学校毕业的,到大学阶段有可能会遭遇学习困难的比率要比普通学生更高。一方面是因为你开始放松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你会发现自己除了考试之外什么都不懂,而大学的课堂上很多前置知识是默认你会知道的,认为在高中阶段你都学习过的,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测试越来越发现其实不是,很多东西他要么没上过,要么因为不是高考的重头戏,所以忘记了。但是高考机器出来的学生,他们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个而受到挫折,他们会觉得自己明明是某个地方的状元,到了大城市的高等学府则举步维艰,就特别容易自我放弃。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话:“我们上课不是为蠢蛋上的,因为他们这些人没有受教育的必要;也不是为天才上的,因为天才自己能开启自己的道路;我们是为中等人上的,中等人希望能够学到知识,并且能够在生活中肩负起自己的职责。”而我的实际想法恰好是和康德悖反的。首先,我不想教傻蛋,真有傻蛋那也没办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去了;中等人我是教,但不会特别上心;我恰恰是希望给天才留下道路。无论是本科教育也罢,或者是研究生教育也罢,我往往会偏爱一些比较优秀的学生,然后为这些学生进行各种联系,搭桥、铺路,因为觉得如果不向他们倾斜,他们的天赋是无法很好地发展出来的。老师有偏爱,这一点对学生来说是否公平,我也不知道。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有偏爱是很正常的,只要这个偏爱是在道德允许范围之内的,那么这就是一件正常的事。
我觉得我们(高校老师)有可能是有职业病,所以在教育方面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却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我自己和诸位一样,在教育问题上,我们现在已经是获利者了,但我和诸位的后代都还要进入现在这样一个中等或高等教育当中。我当然希望教育可能变得更好。离开了教育体制,我们不可能把孩子关在家里教,又不是人人都是郑渊洁可以自己教孩子。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怎么使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好?一方面是能够对中等水平的学生变得更友善,使得他们有更多的准备去面对未来的挑战;另一方面是能够使优秀的天才学生顺畅走上他们自己的道路。我觉得这些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至于犬儒主义,因为作为译者,我可能已经太熟悉这本书所提示的种种问题,反而说不上些什么东西,反而不太愿意从犬儒主义角度去思考自己的教育实践。我只觉得,我这几年从放羊不管,“我是你导师,但是你要愿意做什么,那你就去做什么,你要去自由探索”,到了甚至上场带打,“就你这论文写的什么垃圾玩意儿,马上就要送盲审了,不行,我花三天时间帮你改一下,然后你根据我改的接下去改”;进而我有可能会盯得更紧,极度焦虑,变成了一个无能狂怒的导师,“怎么你们连这个都不知道”,“现在我要开始布置任务了,以下1234点,拿出笔、拿出纸给我记下来,下周如果没有完成任务就不要来见我”。我变得越来越愤怒,任教的一开始是心气平和的,而现在我却越来越像我自己的博士导师,变成易怒的样子。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讲座|倪剑青&郁喆隽:人人都是犬儒主义者?
知识分子对犬儒主义的批评,为何反倒可能助长犬儒主义?
讲座|梁永安&李松蔚&陈赛:《苏菲的世界》,从文字到图像
毛俊杰老公关喆 毛俊杰老公是关喆吗
曹郁姚晨撒狗粮 姚晨晒与老公合照甜蜜庆祝七周年
曹郁姚晨什么关系 曹郁姚晨的关系是什么
齐喆:对工艺美术进入当代空间,我非常乐观
漆培鑫《男狐聊斋3》定档 化身青丘狐族少主白衣清隽俊朗非凡
试问谁能不馋倪妮的身子呢,瘦且有料,身材和气质都是一等一的绝
吉克隽逸为什么爱穿尿不湿 造型一次比一次抢眼
网址: 讲座|倪剑青&郁喆隽:人人都是犬儒主义者? http://www.pyqsh.com/newsview27223.html
推荐社会生活
- 1一个人,也要好好生活 2073
- 2新疆美女哈妮克孜恋情揭晓,男 2064
- 3中华民国双旗开国纪念币一枚能 1836
- 4细读《金瓶梅词话》第35回之 1790
- 5李清照:两处相思同淋雪,此生 1253
- 6金莎的穿搭给人一种精致土的感 1155
- 7周杰伦晒和昆凌游玩照 同和小 1064
- 8据李子柒友人透露,李子柒已经 1051
- 9苏志燮宣传新片不忘撒狗粮,大 928
- 10自毁人生!池子再说无底线言论 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