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从我们的生活中剥离出时间
原标题:安妮·埃尔诺:从我们的生活中剥离出时间
1972年冬末,安妮·埃尔诺和丈夫买下一台摄像机,此后的近十年里,这台摄像机记录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和旅行经历。直到1982年,安妮·埃尔诺与丈夫离婚,摄像机被丈夫带走,浓缩过去这十年经历的胶卷留了下来,安妮·埃尔诺成为它们的“监护人”。

电影《超8岁月》剧照
2022年,这些胶卷被安妮·埃尔诺和儿子制作成电影《超8岁月》,在当年五月份举办的戛纳电影节上首映。五个月后,发生了那件人尽皆知的事,安妮·埃尔诺被评选为第119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学院给出的获奖评语是:“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
在这部电影里,影像中的私人记忆、制作者本人从影像本身发散至公共记忆与时代变化的旁白,几乎都可以看作安妮·埃尔诺写作脉络的显影。在她近五十年的职业生涯里,她从不忌惮将私人经历和她所成长的那个年代的社会图景作为写作的蓝本。
1940年,安妮·埃尔诺出生在法国一个名叫利勒博纳的海滨城市,后来她跟随父母搬到伊沃托。在这个小镇的工人街区,父母开了咖啡馆和杂货店,她在这里度过了剩下的童年时代。在当地的一所私立天主教学校学习时,安妮·埃尔诺遇到了很多跟自己出身不同的同龄人,这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成长于工人家庭的自己与他人的隔阂,这种阶级差异所带来的自卑和疏离感成为她之后文学创作的母题之一。

安妮·埃尔诺
成年之后,安妮·埃尔诺先是前往伦敦当了一段时间保姆,回到法国后分别在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就读。1967年,她成为中学教师,教授法语,实现了父辈对下一代的期望——脱离了工人阶级,步入了在她眼里象征智识和品味的中产阶级。也就在这一年,安妮·埃尔诺的父亲去世,父亲的离世后来促成了她的第四部作品《一个男人的位置》。
至于她的前三部作品,1974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空壁橱》以她在1964年经历的一次非法堕胎为原型,讲述了一个女孩的成长经历。1977年出版的《照他们说的做》和1981年的《一个冰冻的女人》讲述了跟自己同样来自工人家庭的女主角如何在工作和婚姻的帮助下摆脱了出身。这三部小说构成了安妮·埃尔诺早期的自传体三部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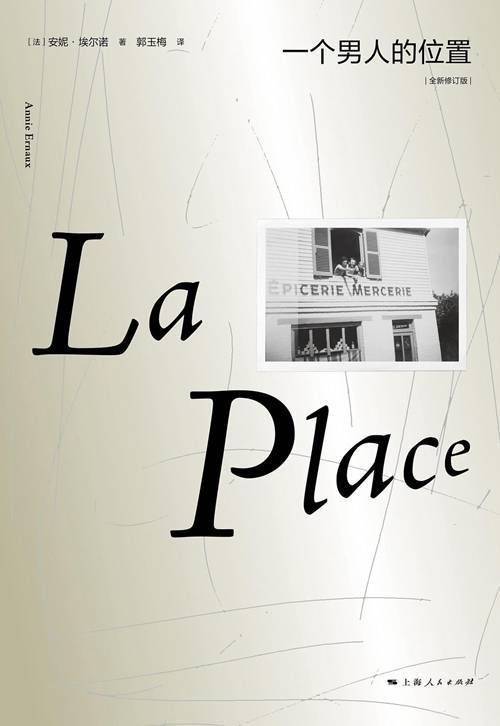
1984年,安妮·埃尔诺出版了关于父亲的作品《一个男人的位置》,她对写作的看法有了变化,她剔除了自传体小说中的虚构成分,开始完全按照真实的记忆记录父亲的过往。这也是为什么她不再认为自己是小说家,甚至不再把自己的作品视为小说,她称自己是“自我的民族志学家”。在这部作品里,她努力尝试从更客观的角度讲述父亲,审视父亲与自己在阶级身份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她痛苦的根源和写作的初衷之一。她的目的很明确:“我要以我的父亲为主题,写他的生活,写我年少时期与他的隔膜,而这种隔膜其实是一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膜,但它又是极其特殊的,不可言传的,就像不得不分手而又情思不断的那种爱情。”
安妮·埃尔诺的父亲出生在雇工家庭,早早辍学在农场主手下打工。一战后,父亲从部队退役去工厂,在那里认识了作家同样出身底层的母亲,婚后,他们开了一间咖啡杂货店,从工人变成了商人,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回想自己的童年生活,安妮·埃尔诺写,“我与寄宿学校里的学生相比,真的是不能说穿得比他们差,当地农民的女儿或是药剂师的宝贝心肝们有的东西我都有”。
然而物质上的成功并不能掩盖父亲因为出身底层、没受过教育所带来的自卑。父亲害怕外出时出丑,他不会写“已阅并同意”只能用“要待证明”代替,在认为是重要人物的面前,父亲总是很羞怯,不敢提出任何问题,担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这种根植于身份和成长背景的心理状态随着安妮·埃尔诺的成长越发明显。试想一下,一个智识匮乏的父亲有一个读私立天主教学校的女儿,他发现自己的女儿开始会讲正统的法语而不是方言,并开始纠正他的发音,他的自卑和失落感也随之放大。而对于当时的安妮·埃尔诺来说,当她在学校接触到出身优渥的孩子,面对你喜欢爵士乐还是古典音乐这个问题时,她的内心感受与父亲是一样的。
或许是因为对阶级身份深刻的探讨,《一个男人的位置》在当时广受好评,并为安妮·埃尔诺赢得了次年的勒诺多文学奖。1987年,安妮·埃尔诺以同样的方式,在母亲去世后写下关于母亲的作品《一个女人的故事》。

作品从母亲去世写起,安妮·埃尔诺记录了母亲在贫困的单亲家庭里长大,先后在不同的工厂里当工人,从小独立让母亲养成了粗暴且不服输的性格,在成家之后,母亲的这种性格为家庭带来了改变——正是在母亲的提议下,他们家有了咖啡杂货店。
与《一个男人的位置》不同的是,安妮·埃尔诺在这本书里表达了对母亲强烈的情感依赖,她写道“母亲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母亲的去世使我用另一种目光来看周围的世界,甚至人们那些习以为常的活动也开始让我不理解了”。
另一方面,安妮·埃尔诺也提到自己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与母亲“割席”。她开始抗拒母亲暴躁的性格以及过分的爱和指责在自己身上的影响,转而关注时装杂志里的女性以及同学们的母亲——那些太太们没有母亲粗鲁的讲话方式和不文雅的举止。但无论如何,在远离母亲的同时她总会意识到她们是如此相像,这一点让她痛苦不堪。她们成为彼此精神上的阶级敌人,却无法摆脱同样的家庭背景下早已捆绑在一起的束缚。
1993年,安妮·埃尔诺的第六本书《简单的激情》记录了她和一名已婚外交官的恋情。1997年的《耻辱》是对成长过程中一些琐碎记忆的展露,如书名总结的那样,这些记忆都跟耻辱感有关。同年,她的另一本书《我留在黑暗中》讲述了母亲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那段时期。她写于2000年的《正发生》在2021年被改编成电影,区别于安妮·埃尔诺第一本以堕胎为主题的小说《空壁橱》,《正发生》没有虚构的成分,她忠实地回忆了自己非法堕胎的经历。

电影《正发生》剧照
由此来看,安妮·埃尔诺的个人风格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极度私人化,几乎以自我冒犯的姿态出现在读者眼前。这种风格让人想起当代另一位甘愿将自己的生活事无巨细地披露在纸上的作家——写出六本《我的奋斗》的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而安妮·埃尔诺之所以将自己称为“内心世界的流亡者”,或许是因为她需要通过写作来理解并分析她与父母、与过去和当下世界的关系。在《一个女人的故事》的开头,她引用让·热内:“我大胆做一个解释:当一个人成为背叛者之后,写作就是其最后的依靠。”
即便这个过程似乎并不顺利,在难以从写作和生活里找到一块自留地后,作家被迫成为自己口中的流亡者。
私人化的写作风格只能代表安妮·埃尔诺的一面,作者之外的她还是左翼知识分子、女性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她曾公开支持2018年的法国“黄背心”运动,反对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的殖民暴行。这些身份在她的作品中又表现为对法国社会、公共记忆和文化的记录与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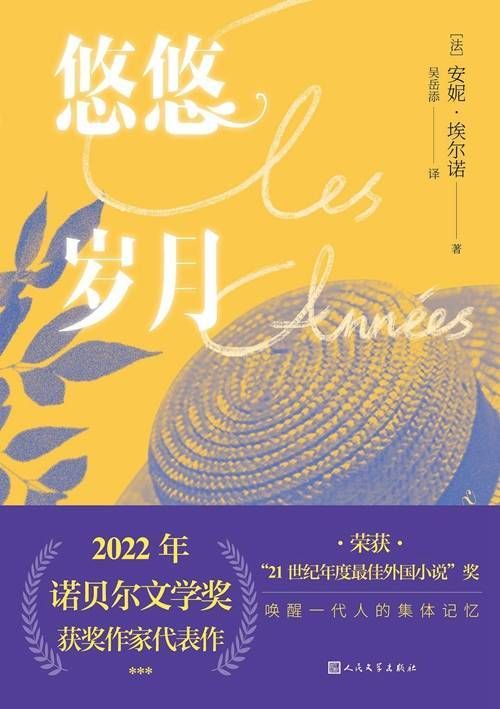
出版于2008年的《悠悠岁月》大概是安妮·埃尔诺最负盛名的作品,拿到了当年的玛格丽特·杜拉斯文学奖,英译本入围了国际布克奖。在这部作品里,安妮·埃尔诺通过一张张照片,勾连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当代,整个法国在个人和集体层面遭遇的变革,其中不乏法国抵抗运动、阿尔及利亚战争、五月风暴等重大事件,也包括堕胎合法化、性解放等关乎女性命运的运动。
这段历史也顺应了安妮·埃尔诺的成长经历,因此这部作品里的许多部分都直接来自她的生活。但安妮·埃尔诺没有将这些记忆归之于“我”,而是以“我们”代替。这也是许多评论推崇她的原因,即是她在这部作品里创作了一种“无人称自传”,一份“公共日记”,从而引起一整代法国人——尤其是法国女性的共鸣。像现任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安妮·埃尔诺获奖表达敬意时所说的:“五十年来安妮·埃尔诺一直在写一部关于我们国家集体和亲密记忆的小说,她的声音是女性自由的声音,也是本世纪被遗忘的声音。”
回到电影《超8岁月》,你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安妮·埃尔诺如何将个人记忆与集体历史结合。那些粗糙又私密的影像绝大部分都出自安妮·埃尔诺的前夫,他记录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安妮·埃尔诺本人,两个年幼的儿子,以及一家人在欧洲大陆旅居过的不同城市。多年后,作为画面里的主角之一,安妮·埃尔诺重新为这一切加以评注。她时常将话题引向七十年代的历史与政治,她也追忆画面里已经消逝的人,自己的母亲和祖父母,站在摄像机背后的前夫,包括孩子的童年和曾经的自己。
而她对这些影像的定义是如此简洁和准确:“快乐而带有一种暴力的色彩……是从我们的生活中剥离出的一种新的时间类型。”这似乎也可以用来形容她的写作,用真实的、根植记忆的语言,从她和我们的生活中剥离出时间,制成放置在真空里的永恒标本,供早已失去它们的人反复观看。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安妮·埃尔诺:从我们的生活中剥离出时间
新晋诺奖作家安妮·埃尔诺:“危险的”女性写作如何可能
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她用手中的笔,救赎苦难的人生
新科诺奖作家安妮·埃尔诺:中译本一年只卖出400本,真的是冷门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安妮·埃尔诺:写作是一种政治行为,让我们打开眼睛看见社会的不平等
2022诺贝尔文学奖花落安妮·埃尔诺 《悠悠岁月》中文简体版正加印
诺奖得主中文版图书热销
新晋诺奖作家的作品好在哪?
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她
卡琳-让-皮埃尔将接替普萨基成为新任白宫发言人
网址: 安妮·埃尔诺:从我们的生活中剥离出时间 http://www.pyqsh.com/newsview27668.html
推荐社会生活
- 1一个人,也要好好生活 2073
- 2新疆美女哈妮克孜恋情揭晓,男 2064
- 3中华民国双旗开国纪念币一枚能 1836
- 4细读《金瓶梅词话》第35回之 1790
- 5李清照:两处相思同淋雪,此生 1253
- 6金莎的穿搭给人一种精致土的感 1155
- 7周杰伦晒和昆凌游玩照 同和小 1064
- 8据李子柒友人透露,李子柒已经 1051
- 9苏志燮宣传新片不忘撒狗粮,大 928
- 10自毁人生!池子再说无底线言论 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