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我们生活的时代,留下一个自己的版本
原标题:她为我们生活的时代,留下一个自己的版本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那个只有东西南北四条街,平凡又独特的川西小镇“平乐镇”?不久前,作家颜歌在进行了许久的英文写作之后,带着暌违多年的全新中文长篇小说《平乐县志》归来,“平乐镇”的故事继续上演。
故事的开篇,一个名叫“陈地菊”的普通女人从繁荣的城市回到自小长大的小镇,或许她和我们一样,在城市中挣扎过,哭过笑过,充满希望又死心过,于是她选择回到最熟悉的土地,寻找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故事的结尾,这个名叫“陈地菊”的普通女人又离开了,她选择再次出走,她觉得也许生活并没有困住谁,就像我们一样,总相信继续向外走就会有点什么不一样。
颜歌笔下的普通人是动人的,他们有了伤心事想哭就哭,哭过就算了,不完美,但真实生动,几乎每个人都能从中看见自己的影子。通过书写“陈地菊”和她身边一众普通人命运的沉浮,颜歌也用文字串起了一座世相起落的川西小镇和它背后的时代。用颜歌自己的话说,她希望“为我生活的时代留下一个自己的版本。”
最近,看理想和颜歌进行了一次长谈,这场对话,不仅仅关于这本小说、关于文学、关于书写,你还能从其中看见,一位女性在不同地域、文化和时代变迁中,如何不断寻找自我,书写自我。
如何用语言表达自我?
“抱歉”,“稍等,让我想想这个词应该怎么说”,大概是对谈过程中,颜歌说得最多的短句。
“很久没有说中文了,我现在生活的环境中,我遇到的事情、发生的困惑,如果用中文说出来,好像是incompatible的,意思应该算是‘不太搭’”。
作为国内知名的作家,使用中文写作20年,也拿过无数赞誉和奖项,2016年,颜歌去往英国,在东英吉利大学学习文学,也用英语进行写作。前段时间,颜歌的英文短篇小说集《Elsewhere》(在别处)出版,现在还会教授英文写作。
这样巨大的跨越不免让人感到惊讶。颜歌坦诚,自己确实很久没有使用中文了。
老实说,写作的人,面对文字久了,会越发熟悉与顺畅,也就是常说的“语感”,使用得越久越是会产生一种共生的依赖关系。如果要到新的语言环境中,如何维持原来语感,都可以想见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谈及要如何面对这种困难,颜歌笑笑说,她不会去“解决”,“我的生活里是没有中文的,在英国我就写英文小说。生活中我是经常跟英文写作小组的朋友来往,我成为了那个群体的一分子,他们都会叫我Yan,好像这是我的新身份。我不会去中国超市,也不吃中餐。感觉现在是我的下半辈子,过去是我的上半辈子。”

Norwich制作的图书雕塑,上面有颜歌的作品《Elsewhere》供图/颜歌
在接受FT采访时,颜歌也提及,在美国、爱尔兰和英国生活后,她发现自己住进了彻头彻脑的“英文环境”里。有一天,她灵感大发,想写一个发生在都柏林的故事,但在她的脑子里,这个故事的人物、对话、情节全部都是英文的,她感到被圈住了,无从下手。最终,她决定用英文来写这个故事。
于是,她向英文“投降”了,“在英语环境里,我干脆就彻底跟中文切断了,我是一个非典型的变态例子,对我来说可能就是太痛了,我就宁愿不要……抱歉,我好像不是一个会鼓励到别人的人。”
如此的决绝不免让人讶异。如今,在这个“润学”涌动的年代,对很多人来说,逃离国内的环境是一种可能的解法。
但颜歌却分享了另一重的真实感受,她最近常常需要与朋友“互相打气”,比如前段时间,她还与旅欧的媒体人、“不合时宜”的主播王磬聊了聊。
在那次谈话中,王磬提及了一个特别动人的观察,“我们到了国外,也许好像混得还不错,但其实是进入了白人的体系中,我们把自己的话语和准则都投入到另一个体系里”。
王磬认为,在当下的新移民潮里,他们应该重新去保卫“我们这些人的中文到底应该是什么”。也许大家可以一起,共同构思如何建立一个在大陆之外使用的中文体系,这个体系有能力去诉说和表达这些人的焦虑、困惑和探索,而不是只使用写作。
这个讨论让颜歌十分触动,是啊,是否可以创造一种新的中文语言,解构掉当下中文话语里,那些被条条框框限制、甚至充满语言暴力的部分呢?
重新去找谁是“颜歌”
虽然使用双语写作,也都在不同领域获得了文学成就,但颜歌并没有很多精英式的话语里通晓多门语言的骄傲感,她谈得更多的是自己的困惑与挣扎。
“一直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人,好像就是百分之百完整的人,完整适应那个环境。一旦选择离开,人生就再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了,不管彻底出走,还是离开以后再回来,都不可能再复原到最完整的状态了。”
颜歌用自己的写作经历进行了诠释,她从2012年就开始构思《平乐县志》这本小说。从2016年去到英国以后,长达四年里的时间里,中文似乎被她塞到了脑海中的一个抽屉里关了起来,只使用英文写作。
直到《Elsewhere》交稿后,颜歌才有精力回过头去继续中文写作。虽然搁置了很久,但《平乐县志》其实一直是颜歌念念不忘的作品,她想要回到平乐镇(《平乐县志》的故事发生地,原型为颜歌的故乡郫县),那是她的“the original”,原初之地。
仅仅在《Elsewhere》和英国出版社签约后一周,颜歌就重新把写了一半的《平乐县志》从自己的文件夹里拿出来。但许久不接触中文,她竟然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陌生感,“我好像不会写作了”。平乐镇系列不只使用了中文,它还是颜歌结合了四川话与本地文化,所构建出来的带有她鲜明的个人印记的叙事方法。
颜歌好像找不到自己的语言了,正好,2020年理想国再版了几本平乐镇系列小说集,寄到了英国,“我反复看自己的书,不是自恋,是在学习,学习这个叫颜歌的人,是怎么写作的,怎么模仿她。”
这样的过程很艰难,颜歌开玩笑说,“如果搜索记录被曝光,那我一定会身败名裂”,由于思维的习惯已经陷入英文里,她常常要返回去搜索一个中文词汇应该怎么写,比如表达母女情深的成语有什么,如何展现心情犹豫。
“像是在用第二语言写作一样”,在艰难写完文字之后,她发现,语言表达层面的困难还只是最表层的,在《平乐县志》的创作过程中,颜歌感受到了更深一层的束缚,那是语言背后暗藏的思维方式的巨大不同。
在颜歌看来,中文写作与英文写作的最大不同,就是时间。
我们在学习英语时,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记忆时态,不同单词的过去时、进行时、将来时。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运用到写作中时,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果仔细思考,你会发现,中文写作没有英文那样明确的时态,甚至可以完全不出现时间的概念——但我们在写作和阅读的时候,却能从文字中推测出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颜歌的多本中文小说都被译成了英文,翻译在将《我们家》翻译成英文时,对颜歌提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when did it happen”,这件事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当时颜歌很想回答她,为什么要这么在乎时间,我们不就是活在混沌中吗?
颜歌的爱尔兰丈夫看了翻译后的《我们家》,也感到特别惊讶,说自己“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小说,感觉整个时空都在旋转”。由于翻译成英文必须加上时态,所以这本书好像就不停地在不同的时间里进进出出。
在用英文写作时,颜歌面临的终极挑战之一,也是时间,她总在不断地追逐时间。
在英文小说里,不管用怎样的方式进行写作——即使是再意识流的作品,时间结构也依然是故事依托的根本。在英文写作中,时间是一种逃脱不掉的存在。
带上了这种视角,颜歌发现,中文小说,尤其是自己过去的作品,思维的基本框架不会是时间结构(temporal structure),而常常建立在特别的空间结构(spatial correlation)之上。
所以,从英文写作再回到中文写作时,颜歌感觉自己“被时间的铁链困住了”,不再是过去那样在时间里自由自在的的状态。
她甚至有点绝望,自己已经无法摆脱时间的烙印,英文写作里有个概念叫作“signposting”,特别表明了英语创作里对清晰性的要求。如果时间状态出现了变化,比如从过去回到了现在,需要把它标记(signpost)出来,像一个路标一样指示时间出现了变化。
现在进行中文写作时,颜歌总是不自觉地像英文那样思考时间的概念。这让她感觉“僵硬无比”,再也写不出以前那种漩涡一样的时间状态了,“这就是英文写作带给我的血的教训”。

《勃朗特姐妹》
对于这个转变,颜歌坦诚,自己并不会去和解,就让时间铐在自己身上。只是通过这点,她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不同语言之间的巨大不同。“当我们呆在一个环境里时,其实我们不止在使用同一种语言,我们还共享了一套历史文化,有同一个上下文。
一直生活在同一种语言和生活环境里时,有点是前现代的状态,农耕社会那样,天、地、人都在一起,是和谐的。但脱离了原来的语言后,人和天地之间的联系断裂了,人被带离了土地,这像是一种从现代进入后现代状态。”
不过,对于这种损失,颜歌倒也并不会完全悲观。“是的,你永远都会缺失一部分,不过人可以去综合衡量得与失,再去做(出走)的决定。”因为世界各地都有各自糟糕之处,不存在一个真正完美甚至接近完美的地方。但只要愿意承担后果,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被时间困住之后
在意识到“时间”的存在后,颜歌不仅专门写了一篇论文,讨论这个中文与英文写作中的巨大差异。她身体力行地发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差异,最终形成不同的文学体系,也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价值和判断。
于是,颜歌在自己身上进行了实验和尝试,比如在用英文写作时,她有意识地对抗“时间”这种英文写作的传统,而采用空间来构造叙事。
还有一次,她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借鉴中国古代小说写作了一篇英文短篇。在这篇《Traveling In The Summer》中,颜歌加入了古典中文小说里的叙事闲笔以及委婉表达。在中文体系里,那些难以名状的部分常常有着独特的美感,但这却让英文编辑感到困惑,这到底想要表达什么?颜歌却十分坚持,最后她说服了编辑保留了这些部分。
“这就是我‘黑化‘的开始,现在‘黑化‘得更彻底了”。对颜歌来说,英文只是一种“写作工具”,她希望,最终可以在英语小说里建构起一种“反英文”的写作传统。
后来,她做过好几场主题为“Writing Against English”的讲座。不过颜歌强调,跟更中庸、会把一些词看得很重的中文语境不同,在英文里,很多时候“against”并不是一个那么有对抗性的词汇,可以表达很中性的意味,所以,against并不意味着单一的、二元对立的“抗争”或是“对抗”,直接翻译成“反”更合适。
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这样用反英语的方式来使用这个“后殖民语言”进行写作——颜歌解释说,英语现在成为世界语言,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后殖民结果。所以,使用英文写作,并不意味着就要投身到旧有的英语文学及其思想体系中,也可以建构起“literatures in English”,用英语写作的不同文学。
许多作家就此进行过深度探索,比如近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大热门,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早在1968年,他就写作了一篇名为“On the Abolition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废除英文系)的文章。
在欧美接受过英文写作训练后,恩古吉将自己的名字从詹姆斯(一个典型的白人名字)改成了恩古吉,在肯尼亚语里意为“文学”。他还回到内罗毕大学,将英语文学系改为非洲文学与语言系,推动肯尼亚的语言文学革命。
在后殖民主义的经典著作《精神的去殖民化》(Decolonizing the Mind)里,恩古吉思考,“如果真的有必要学习某个单一文化的历史谱系,为什么不是非洲文明呢?”他认为,“英语属性”是一颗文化炸弹,“消灭了一个人对自己名字、语言、环境、抗争历史、团结、个人潜能和根本上对自己的信念。它让人们把自己的历史看作一无是处的废墟……驱使人们去认同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比如,其他人而非自己的语言”。
不管是使用其他语言进行写作,还是尽力把英文思维“去殖民化”的过程,都是在反对语言霸权带来的否定,去寻找真实的自我。

《紫色》
这样的意识被越来越多人接受,比如在2020年,经过多位教职员工的投票,康奈尔大学最终把英语系(the English department)的名字改成了英语文学系(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s in English),一方面是为了消除歧义(English也指英国人),更重要之处在于词汇“literatures”使用了复数形式,这或许是在强调,多远族裔和人群用英语写作的文学,也需要被纳入到英文写作的范畴中。
过去常常有一种声音,好像用英语写作就只是“给白人看的”。但这种观点其实有点过时了,现在的英文写作,存在许多实验性与自我探索的部分。
比如前几年诺奖得主石黑一雄,阅读他的小说,尤其是像《别让我走》《克拉拉与太阳》等中后期的作品,会发现从文字中几乎看不出他的国别,他的族裔,甚至他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石黑一雄的小说是世界性的。
石黑一雄5岁时就与父母一同移居英国,他在英国长大、也一直使用英文进行写作,但他的早期的作品仍有比较多日本元素。石黑一雄说过,“我好像需要把日本的故事写完,满足大家的期待以后,我才能去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颜歌认为,这其实是许多少数族裔作家的普遍困境,处在一个白人主导的社会里时,不可避免的会被他者化地凝视。比如她常常感觉到,自己被看作是一位“亚洲女性有色人种作家”,或者更简单粗暴的标签,“一个中国人”。
这时候,人的个体性好像被抽离了,成为了一种身份的代表,一个身份政治的符号。有趣的是,颜歌与石黑一雄读了同一所大学,作品都在同一个出版社出版,甚至和同一个编辑合作。有一次在出版社年会上,石黑一雄还很好奇地问颜歌,为什么会选择用英文进行写作,或许因为这是大家共享的困惑。
从婴孩到成人,其实一个人逐渐建立自我、培养自己个体性的过程,多年的小说写作,也构建了颜歌的作家身份,但来到英国时,从一个文化环境到另一个文化环境里,过往多年建构起来的个体性却好像都被剥夺了。
“这其实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她似乎重新变为一个婴孩,必须要重新用英文写作来建构自己的新身份,去确认自己的真实性和原创性。
颜歌的少部分朋友同时阅读过她的中文和英文小说,不止一个朋友评论说,在两种语言的小说里感到了强烈的分裂感,甚至阅读出了一种随机性,好像“颜歌”成为了一个多元宇宙,不同小说体现着她的不同人格。
“我感觉自己真的有点人格分裂了”,颜歌笑了笑。对于这种分裂,她有时候很悲观,有时候又很乐观。
悲观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像是在炼狱中,处在一个“不左不右、不上不下、不男不女、不东不西”状态里,好像卡住了,有时候感觉十分孤独。不管在哪里,她都没法回到百分之百的状态。不管处在哪个语境里,都需要不断地自我解释,而无法只用语言就能表达自我。
乐观时,她又觉得自己很幸运,“好像我这辈子拥有了两次人生,有两个作家的身份,有两个文学世界,甚至得到了重生”。
尽量去呈现世界的肌理
重新写作《平乐县志》,似乎也是一种在不同人生之间转换的过程。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参照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一般简称“二拍”)的语言风格进行写作。

写完《平乐县志》的写字台的墙,供图/颜歌
多年英文写作之后,颜歌一直在思考,一种语言背后的社会文化、历史根源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才是中文的文学传统和叙事传统,它又携带了什么?
于是,她越发渴望在中文写作中,体现中文性与中国文化里的文学传统,因而对“二拍”的参考也并不奇怪了——这毕竟是中国古典短篇白话小说的巅峰之作。
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最初构思《平乐县志》写作的时间是2012年,对于如何书写当下,颜歌是十分困惑的。那时,每天好像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各种意识形态与社会价值的激烈碰撞,每每让人感到喧哗与浮躁。颜歌认为,这种社会状态恰恰与“二拍”的成书的时代颇为类似,那是在明朝末年,“三教九流”开始萌芽,人们都在无序中寻找有序。
不过再往后十年,也就是断断续续写作《平乐县志》的十年中,产生了更强烈的剧变,这让颜歌遭受了强烈的存在主义危机,她甚至不断会有自我怀疑,写作还有意义吗,这一切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对于这个拷问,颜歌没有给出具体回答。或许,本来这种疑问就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也不是在某个阶段,好像就突然打通任督二脉就能一劳永逸地理解,人似乎总要在疑惑与清明之间不断循环。
虽然早就开始写作,但颜歌一直没有想明白女主角陈地菊的最终结局。这是颜歌写过的最难写的人物,她一直搞不懂,陈地菊到底应该是一个怎样的人。
继续写作《平乐县志》后,当小说进入到收尾阶段,新的平乐镇正在建立,世界发生了巨变。现实中,那是在2020年之后,世界也正在剧变,病毒肆虐,大家都被困在家里,很难看到希望,也罕见真心的喜悦,颇有种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颜歌终于想明白了女主角陈地菊的最终决定,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陈地菊好像活了过来。于是她转过头去,删掉了一大半文字,重新写作了目前的小说。
许多读者评论中,都感受到了《平乐县志》体现的那时普遍的苦楚悲凉、无助以及绝望。颜歌的书写不仅记录了自我所感,也更是体现了时代变化在她身上留下的刻痕。
除了“二拍”的语言风格,《平乐县志》另一个独特之处,来自于书名。如果阅读过地方志,尤其是县志,你会发现里面全是各类琐碎的、事无巨细的记录。比如某年当地产了多少种水果,或是开了多少家美发沙龙。

《小妇人》(1994)
对颜歌来说,县志是一个“神奇的存在”,当然背后还是有权力的因素,但县志记录的内容,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一个去中心化、去权力化的过程。
县志会把社会的方方面面,尽量不加选择、几乎不带歧视地收纳进来。在同一本县志里,会同时记录郫县县长换届和郫县美发店老板数量几何,社会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许多在主流历史里籍籍无名的普通人,也被县志所收录。
这类数据也许绝大时候都被封存起来,鲜有人知晓,使用的时机也许很少,但它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记录本身就十分重要。在去英国前,因为想撰写平乐镇的故事,颜歌专门去到郫县县志办要了许多县志,那里的工作人员十分惊讶,竟然还有人想关心这些内容,便十分热情地给她拿了许多资料。
在这些厚厚的资料里爬梳时,颜歌突然意识到,小说家写作是在进行选择性的叙事,而县志很大程度上是不选择的。写作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而她试图去反思这种权力。
所以颜歌在《平乐县志》里,参考了县志的数据与写作方法,试图去写作尽量多的人物,即使有几个笔墨更集中的视角人物,但也会经历从他们铺开,展现更多群像与社会的肌理。
在人物写作时,颜歌也努力地不评判,而用白描来呈现人的复杂性。她小说的每个人物都有着很明显的缺陷,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正面人物,以尽力消解习惯性的道德评判。
颜歌认为,小说家是一个装故事的瓶子,小说家的职责是去呈现这个世界的肌理,让世界本身来引导故事行走。作者要尽量隐形,不要评判,最好化成风消失在故事里。
不过她也坦诚,理论如此,实际很难做到。就像她在仿照“二拍”里的说书风格时,不自觉地会思考其中的厌女部分,她的选择是干脆放大这种声音,体现这种声音里对男女性别不同从而评价不同的偏颇。也许这样,读者阅读时就会产生不舒服,进而也去思考,生活中那么多的“理所当然”里,到底蕴含着多少不公正与偏颇呢?
这是与过去的告别
短期之内,《平乐县志》将是颜歌的最后一部长篇中文小说。“这是我的告别作”,颜歌在多个场合都有类似的表达。
如果稍微多看过一些颜歌的小说,会发现她一直在写平乐镇,也就是她的故乡四川郫县,那个产豆瓣酱的郫县。
最早一本是于2008年出版的《五月女王》。2004年,颜歌的母亲去世了,之后她开始写作平乐镇系列,这是她写作生涯中时间跨度最久、也投注了最多个人情感的作品系列。
从私人角度来说,颜歌感觉自己始终无法走出母亲去世这个节点,所以她希望在平乐镇系列小说中,尽量去还原母亲在时的那个世界,捕捉那个世界的肌理,那个世界的人事变迁与喜怒哀乐。
颜歌常常在想,如果母亲没有去世,很可能她就不会离开中国,不会到英国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Elsewhere》里也有关于“mother tongue”(母语)的内容,“我有种深层痛苦,就是没有办法再讲母亲的语言了”。
在写作《平乐县志》时,颜歌把时间设定在2004年之后,写作这个时间点之后的平乐镇。在这部小说里,她将此作为一个平行世界,投入了自己最渴望的期许,陈地菊的妈妈得了癌症,然后奇迹般地康复了。
“我在中文写作里面有一个坎,就是我走不出平乐镇”。所以完成《平乐县志》,也相当于一次自我斩断。她进行英文写作,“重新投胎再过一辈子”。
现在,颜歌着手创作着一部已经的签订英文长篇小说,在写作完这部小说之前,她不会再进行中文写作了。
但如果之后再写,她确定自己不会再写平乐镇,也不会再使用四川方言建构的小说叙事了。颜歌还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也许,她会去尝试构建,一种异国他乡的全新的中文。
采写:青鸾;排版:欧阳咻、野猪;策划:看理想新媒体部,理想国经授权转载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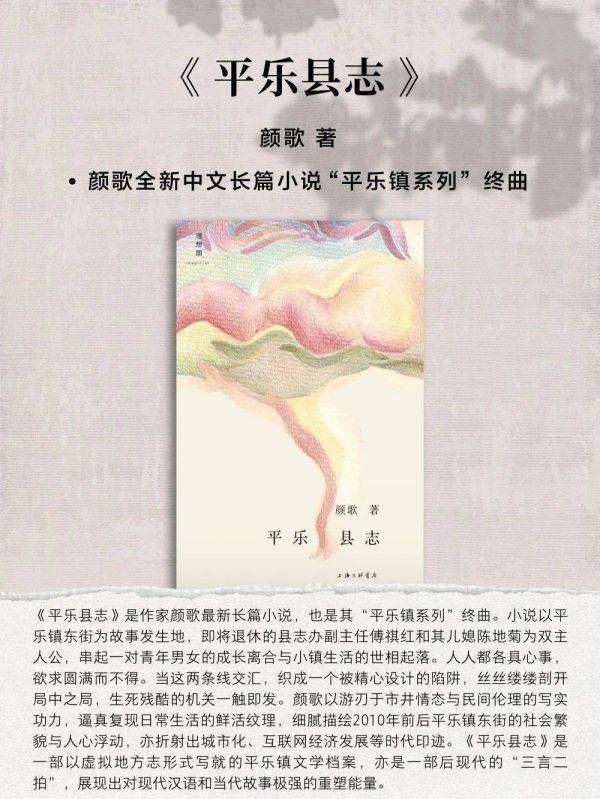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时光之刀留下的时代之伤
一个人不开心的根本原因:把自己活反了
惠特曼:不比我们更高或更低,而是与我们一样,彻底属于自己的时代
安妮·埃尔诺:从我们的生活中剥离出时间
《以X为原型》:审视我们的生活
《自我决定的孤独》:一部关于孤独的当代生活诊断书
杨庆祥《一种模仿的精神生活》:我们在过怎样的生活?
在快时代里留痕慢生活,何大齐“老北京风情”图文结集出版
“若有一部描写我们这个时代全部生活的小说,该有多好啊”丨书评
当她们用文字“整理”自己的成长经验 “生命的写作”就开始了
网址: 她为我们生活的时代,留下一个自己的版本 http://www.pyqsh.com/newsview54749.html
推荐社会生活
- 1一个人,也要好好生活 2077
- 2新疆美女哈妮克孜恋情揭晓,男 2076
- 3中华民国双旗开国纪念币一枚能 1843
- 4细读《金瓶梅词话》第35回之 1796
- 5李清照:两处相思同淋雪,此生 1260
- 6金莎的穿搭给人一种精致土的感 1163
- 7周杰伦晒和昆凌游玩照 同和小 1071
- 8据李子柒友人透露,李子柒已经 1055
- 9杨幂不一样的写真,感觉又看到 944
- 10苏志燮宣传新片不忘撒狗粮,大 9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