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对谈毛尖实录:写小说的人,把光照到暗面
原标题:格非对谈毛尖实录:写小说的人,把光照到暗面
4月20日下午,新京报书评周刊联合译林出版社,邀请作家格非、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在上海思南文学之家围绕格非的新作《登春台》展开对谈,共话“在人群与孤独之间”。
《登春台》是格非在2024年3月出版的最新长篇小说,小说涉及四位主人公,来自江南笤溪村的沈辛夷,来自北京小羊坊村的陈克明,来自甘肃的窦宝庆与来自天津的周振遐。四个人物阶层各异,命运的齿轮却彼此咬合,微尘一刻不停地微弱震动,连起前后四十年的漫长故事。
人生如钟摆,始终在无聊和痛苦之间摆荡。今天的我们面对万物互联的世界,却常常在人群与孤独之间徘徊。对谈中,毛尖与格非围绕小说,谈论了小说的创作,以及在人群与孤独之间的种种摇摆不定和微妙心理。对谈提及了社会的厌老情绪,格非谈到了他在塑造老年角色的创作立场:写作的人要问问自己内心,到底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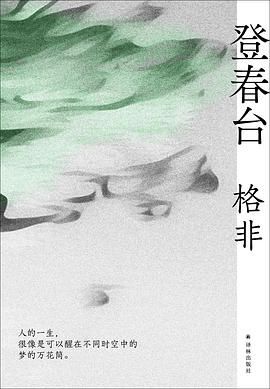
《登春台》
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对谈嘉宾
格非
中国当代作家,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以及《望春风》《月落荒寺》等,中短篇小说《褐色鸟群》《迷舟》《相遇》等;另有论著和散文随笔《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博尔赫斯的面孔》《小说叙事研究》等。
毛尖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家。著有《非常罪,非常美:毛尖电影笔记》《有一只老虎在浴室》《夜短梦长》《一寸灰》《凛冬将至》等二十种。
“可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
毛尖:格非老师在写书的时候是不是说过一句话——“我现在要写下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本书了”。
格非:这个话我大概说过,那时候还没完成这部小说,回老家时同学来庆贺带了点好酒,喝完问我写得怎么样。我说可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十年前李陀曾对我说已经老大不小了,不能随随便便写作了,因为后面时间不多了。那时候我大概五十岁左右,觉得自己还是年轻人,没当回事。可是后来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尤其是这些年。写东西是非常艰巨的劳动,同时是不可多得的巨大快乐。我会把它当成最重要的作品来写。
毛尖:接下来这个话也是他(格非)说的,在一次讲座中说的。他说能写的东西全都是不能讲的东西,所有想说的话都是空缺的,文学作品里最重要的不是作家说了什么,而是他没有说什么。我自己很喜欢或者同意这句话。
格非:这个话最早是福柯说的,福柯1969年在巴黎有一个演讲《什么是作者》,后来意大利学者阿甘本写了一篇文章专门阐释福柯的这次演讲——《作为身姿的作者》,阿甘本看来,作者在作品里的声音不是说话,它是身姿。你要辨别作品里的身姿,而不是人物说了什么,这是不可见不可说的东西。
毛尖:《登春台》翻开目录一共四章,每章的名字是一个人名,都是主要人物。但我自己看《登春台》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印象,没有出现在章节名上的人物特别闪闪发光。所以,是不是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可能比主要人物还重要?
格非: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关系,巴赫金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说过大致相同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人会把最重要的观点放在次要人物身上,甚至坏人身上。在《登春台》这个作品里对我来说不存在次要人物和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有时候是过场人物,有时候行为语言不多,但这些人物我特别难忘。
比如《登春台》里有一个人物桑钦,大家还记得的情节吗?第一章里,下雪天,沈辛夷(主角)去还愿,出来打不到车,最后一辆黑车突然顶着一车积雪停在她跟前,她一上去吓了一跳,这个车不是一般的车,极其豪华,而且开车的人(就是桑钦)装扮还不一般。这个人跟她聊天,聊天的时候转过身问了她一个问题,你知道《水经》这个书是谁写的?沈辛夷说我只知道《水经注》是郦道元写的,但是原作不知道,桑钦没有说话。
这段描述很多人看不懂,我的邻居还问我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其实《水经》的作者本名就是桑钦。桑钦在作品里的设定就好像没有这个人似的,我很喜欢,有点虚幻,在作品里占的篇幅很少,也像谜一样消失了。小说里人物确实都承载着某种特殊的功能,因为小说是对话的机制,主要人物有点像故事的构架,而次要人物也特别重要。

对谈现场(译林出版社提供)
关键的第三章
毛尖:格非老师在小说中写了四个主要人物,四个主要人物有四组关系,沈辛夷和她的妈妈(第一章),陈克明和他的妻子(第二章),窦宝庆身上背负一个案子(第三章),周振遐和恋人的关系(第四章),这四个章节之间串联了非常多重的社会关系,包括母女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情人关系,这些关系彼此又串成了很多人和人群的关系,代际关系、罪与罚的关系、爱和不爱的关系等等,非常庞杂。这么多人物,涉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各阶层,不同的区域,你在设计这些人物的时候,你的考量是什么?
格非:社会性的角度肯定是有的,长篇小说不能不考虑社会性,所以会考虑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区域。这个小说一开始确定的有四个不同的地方,至于选择什么地方,这当中有很大的变化。比如我为什么写甘肃?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在清华当教授,他老跟我讲他们甘肃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神奇。我知道中国农业文明的发祥地在甘肃。说起来我们这家这脉根源在甘肃,我对甘肃有一种特别的亲近之感,所以专门去了甘肃。
毛尖:有没有考量到流量的问题,比如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看罪犯故事?
格非:犯罪这个题材的作品,是现代文学里最多的。传统社会远去了,人们开始进入现代社会。怎么描述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罪恶,这个当中有非常多可以讨论的问题。类型文学都把犯罪题材作为首选,你(毛尖)做电影研究,电影里太多了。
毛尖:80%的B级片都有犯罪情节。
格非:但我写《登春台》不是考虑流行文学因素,是不是增加点犯罪,让色彩感变得更好,这绝对是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四章之间,非常关键的第三章要怎么写。
毛尖:第三章很冒险的,用了第二人称写。
格非:古典音乐四个乐章,第一乐章主题出来,第二乐章呈现强化主题,第三乐章一定和前面两个乐章不一样,它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动力使得四章之间构成有机的关系。到第四章的时候力量感必须强,行动力更强。所以写作的时候,一开始就确定了这个人(第三章的主要人物)是杀过人的。他怀揣着一个秘密来到北京,来到北京的时候人已经杀完了。这当中会有一种强烈的紧张感,希望第三章刚开始看,你(读者)就会被紧张感牢牢地抓住,让阅读在节奏上发生变化。第三章是黏合剂,奇峰突起,照应前两章,为最后一章留出余地。第三章变得很激越,第四章的平静才有力量。
《金瓶梅》与《红楼梦》
毛尖:中国作家中会写男性的作家很多,比如余华特别擅长写17岁出门远行的少年,莫言比较擅长写中老年男人,全类型女性写得好的是格非老师。这个和这么多年你一直在阅读《金瓶梅》《红楼梦》是不是有关系?格非写过一本关于《金瓶梅》的书叫《雪隐鹭鸶》,《金瓶梅》专家都觉得写得特别好。你笔下的女性人物特别光彩夺目,是不是因为在中国巨大的变化中,女性是最能抗得住变迁的,女性身上有更稳定的东西,让你觉得离永恒更近?《红楼梦》《金瓶梅》的阅读让你对塑造女性有特别的体悟吗?

《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
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格非:《雪隐鹭鸶》是我自己写得比较舒服的一本书,我读《金瓶梅》读的时间很长,里面的人物力量感十足。《金瓶梅》只要潘金莲说话,就美得一塌糊涂。比如家里来了一个算命的老太婆,吴月娘说姐妹都去算算命,潘金莲不在。吴月娘见到潘金莲说今天来了一个算命的,把我们每个人的命算得很准,那个人很有一套,可惜了,你不在,你在给你算算。潘金莲说我这样的人,路死路埋,沟死沟埋。我这样的人算什么命,死在什么地方就是活棺材。她的话非常漂亮,直截了当,非常到位,很有力量。
塑造女性形象,《红楼梦》对我影响也很大,读《红楼梦》的时候我很小,大人的秘密话说半句,这个世界变得如此浩瀚,我一个小孩,无缘侧身其中,恨不得自己赶快长大。你刚才讲女性问题,古今中外都一样,只要是男性作家,一般来说都会把女性的形象转化成最理想的东西。曹雪芹也是如此。曹雪芹写《红楼梦》是因为他不愿意让那些女孩子被淹没。今天这个社会变化使得笼罩在女性身上的光环不那么灿烂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仍然是很大的寄托。
毛尖:你讲了很多,我非常喜欢潘金莲这个角色,你会觉得林黛玉是潘金莲的变体吗?
格非:毫无疑问,潘金莲身上很多东西到了《红楼梦》被剔除了,但是潘金莲爱吃醋、爱嫉妒、使小性子、泼辣等性格都被放到了黛玉身上,潘金莲残忍的一面黛玉没有。再比如西门庆,我认为西门庆最后到《红楼梦》变成了贾宝玉。《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不是最坏的人,这个人有一个特别奇怪的设定,他是很天真的人。张竹坡(清代文学家)评价《金瓶梅》的时候把《金瓶梅》的人物分成两类,一种情深之人,一种叫情浅之人,中国社会最可怕的是情深之人,深不可测,对所有的民情人情了如指掌,自己伪装得很到位,隐藏得很深。西门庆是情浅之人,有时候天真烂漫,他天真的一面被贾宝玉继承。《金瓶梅》的人物到了《红楼梦》不是平行移植过去,它做了很大变化,虽然做了变化,但还是可以看出痕迹。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借鉴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它会化用,会做参差的补充。

把光照到暗面
毛尖:《登春台》作品中,格非老师写到非典型的爱情,是因为典型已经不够用了,已经穷途末路了,还是非典型可以让你扩展到更大的人群中,是一种写法的考量?
格非:你说有两种爱情,一种典型的,一种是非典型,我没用过这个概念,但是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比我概括得准确。我原来的概念里,爱情对我来说分成两种,一种是实现了,一种没有实现的。一种完成了,一种没有完成的,或者完成以后又丢失的,需要通过追忆找回来的。古代的文学创作在写爱情的时候,大多会重视实现了的爱情,即便没有实现,也给你很大安慰,所谓有情人终成眷属,因为古人有非常美好的理想和愿望,觉得有情人寄托了他们对男女情爱最美好的愿望。到了今天就不行了,今天这个社会中有很多的事情不可能那么如意,很多事情实现不了。
我在清华跟学生上课有一次课后跟学生聊天,发现学生现在有些问题不太能理解,比如他们读纪德的《窄门》,觉得读不太懂,写的到底是什么?我说这就是单相思,这就是没有实现的爱情。他说没有实现的爱情是什么?我简单讲了一下,爱情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都是没有实现的,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爱情的强烈,对我们这代人(60后)是非常普通的经验,到了今天它发生很大的变化,要考虑成本,考虑时间成本,一个谈不成换一个,它不会像过去讲所谓死生相依。这个东西在不断地变化,到了现代小说,绝大部分的爱情都是非典型的,不可能是非常完美的。虽然爱情的状况不是很如意,在今天有很多事情发生变化,但是我认为它作为一种不可见的东西,或者很困难的东西,仍然是值得追求的。
毛尖:格非老师说现在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核心家庭也面临非常大的变化,比如在我自己童年时代,如果隔壁邻居说他们家爷爷奶奶被送到养老院,我们会觉得这家孩子是有问题,现在把父母送到养老院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格非:这个问题既是古老的问题,也是新问题。很多人想古代社会很好,今天小孩都不行,不愿意赡养父母,把老人扔到养老院,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古代社会这种问题早就出现了。《红楼梦》里有句话,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曹雪芹那个时代就开始发出这种疑问。很多人说中国古代人均寿命三十岁,但我不认可,如果排除战争的影响,一般五六十岁会有的。
毛尖:北宋一段时间有六十到七十岁。
格非:我小时候印象村里全是老人。过去一般正常的老人离开世界的年龄是五六十岁,五六十岁的时候孩子多大?三四十岁,正值壮年。今天是什么情况?今天是六七十岁的人在伺候八九十岁的人。他自己已经一身的病,有的人还要照顾孩子。最近我到医院看家里人,过几天抬走一个,你看着老人躺在床上没有任何生活质量,你作为儿女,你不光要付出体力和心力,不光付出金钱、医疗费,同时你心里会有一个最大的纠结——他还躺在那,人事不省,过很多年,医疗完全可以维持,可是你能每天守候在边上吗?这是社会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这些事情在今天发生了,怎么办?我们今天有一种说法,老人老了那就去专业养老机构,两个礼拜看一次,比如阿尔茨海默症,中国有很多养老院治疗阿尔茨海默症,年轻人觉得社会是这么发展的。作为写小说的人,小说更多考虑的是社会暗的一面,今天的老人正身处暗的一面。我写《人面桃花》的时候有一个读者说这个老头很不正经,我那时候才三十岁不到,只不过我头发白得比较早。现在都是年轻人的世界,有一种厌老的情绪。
毛尖:我看你写的沈辛夷,她有一个对她盘剥蛮厉害的妈妈和弟弟,这种人物特别多,妈妈特别讨厌,我们影视剧经常这样表现,家里女孩子为家里的男性做出贡献。格非写的沈辛夷挺不同,在小说的最后,是以沈辛夷和母亲贾连芳的告别作为结局,而在整个小说中,格非好多次向对女儿盘剥的妈妈伸出援手。当你用你小说家的笔墨照亮这个人物的时候,是不是多少有点因为“你是最后一代把父母扛在肩上的人”,不忍心把这个人物写坏?
格非:贾连芳这么一个人物,她一辈子为儿女打拼,也把自己榨干了,最后到了养老院,还想为女儿积攒嫁妆的钱,她已经得了癌症,离死可能只有两三个月,沈辛夷完全知道她母亲两个月以后离世,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有良知的人,你会反过来把这个光投到阴暗面的。我采取的立场是反过来从老人的一面、从贾连芳这一面来理解她的生存,她的痛苦,巨大的痛苦。她每活一天就少一天,而且没有希望,得了重病躺在病床上的人,每天和护工在一起,那些护工跟他们开玩笑,医院的病房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一个老人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离世,他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生命终结在这个时刻,你也会老的,你也会经历这样的离去离别。这个当中,写作的人还是要问问自己内心,到底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写作千万不能想当然,生活没有那么简单。

对谈现场(译林出版社提供)
在人群与孤独之间
毛尖: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可以过重阳节了,45岁以上重阳节餐厅可以打八折,老也有好处的。
格非:从我的立场上来说,我觉得老年应该是非常愉快的,我觉得这个社会基本不怎么管一个老人,而这正好是我需要的,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由。我们今天很多老人惶惶不可终日很大的原因在于没有自己的乐趣,比如我母亲,她完全没有建立自己任何爱好,心思完全在儿女身上,她从来没有为自己考虑过,你让她一个人独处,找不到任何乐趣。对于我来说,假如我身体还可以,如果能活到八十岁,还有二十年,这些时间可以读书,一般老人总会有一些积蓄、生活保障,就算没钱,你也挣不到钱了,也死心了,踏踏实实过穷日子,省点心。从我自己来讲,反而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我并不害怕孤独。
毛尖:格非老师都点题了,在人群和孤独之间。在看小说的时候,我会看到小说里的人物,一直在人群和孤独之间摇摆或者关联,比如小说最后一章周振遐,一方面非常渴望和人发生连接,但是一方面又很怕和人群发生关系,他一直有矛盾的关系,包括女邻居送他东西,有时候直接扔掉或者让这个东西腐烂掉,小说最后他也接受了女邻居的骚扰。整个文本蛮像在人群和孤独之间的状态,小说中的四个人都是彼此孤立的,正因为他们孤立,他们和人群的连接显得历历在目。
小说中四个人,如果用今天流行的说法I人E人,有两个人是I人,最后反而变成了E人,前面有两个是E人状态,小说最后变成了I人。I人是内向的人,E人是外向的人,这样的划分方法,你觉得有效吗?小说中的I人和E人的流动,你觉得这其中有怎样的辩证法?
格非:我们不用E人I人,咱们就说内向外向行不行。
毛尖:I人E人年轻人听得懂。
格非:我第一次听到。
毛尖:现在走红毯都有I人通道E人通道,如果你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你该走哪条通道。
格非:我觉得内向外向按照心理学的研究,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好像内向外向是天生的,是人的某种性格性情,带有遗传因素。不能说它完全不对,可能有一些道理,但是现在心理学研究社会学研究都已经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所谓内向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性造成的。我认识几个朋友,他们在我看来原来都是特别E的人,非常乐观豁达,这些人无一例外,最后都变成不愿意说话的人,很沉默寡言,整个人从头到脚都变了。为什么?因为他连续遭遇不幸,这说明社会性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人格,导致某个人从一种类型转向另外一种类型,但是窦宝庆不一样。
窦宝庆本来是很正常的,他是很平衡健康的人,因为有了一个秘密,他杀了人,这个东西迫使他转向内向,他又需要隐藏自己,又必须获得社会性,所以他见人就笑,他获得了一种虚假的社会性,让别人看起来我这个人没犯罪,我身上没有什么案底,看上去像一个正常人。他用了一个方法,见人就笑,笑得别人毛骨悚然,外表上不断给别人他是外向的人、很友好的印象,但实际上他内心怀有巨大的恐惧。所以他是外表很E的人,内心很I的人。
周振遐相反,小说里第四章写得比较清楚,他从小被母亲抛弃,母亲嫁给当地公社书记,把小孩打发去了天津,送给伯伯。这个小孩在天津长大,他已经很懂事了,知道被母亲抛弃了,所以他拒绝回家看望母亲。母亲临死的时候要他回去,母亲也在想念这个孩子,但是没办法,回去已经见不到他的母亲了。他被养成了一个孤独的性格,他独处的时候觉得很自在。周振遐和窦宝庆相反,他在孤独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希望孤独。他的身上有点卡夫卡的影子,卡夫卡是处在孤独当中,但是无时无刻不想融入这个社会。小说的结尾,周振遐有一点点向另外一个方向靠近,小说里有一句话,周振遐不是讨厌某些人,是讨厌所有人。他愿意一个人待着,他最后也在朝自己的反面走。
普鲁斯特问卷环节
读者投票选择了普鲁斯特问卷中的部分问题
由毛尖向格非现场提问
毛尖:你认为最完美的快乐是怎样的?
格非:听音乐,我最大的爱好不是阅读,欣赏音乐可能是我最稳定的快乐来源之一。
毛尖: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格非:我自己有时候不太会拒绝别人,决断力是我最需要的,有决断力去把一个事情结束。
毛尖:小说家不应该有这种才华。
毛尖:你最恐惧的是什么?
格非:我已经失去意识了,但是还活着。
毛尖:还在世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
格非:我老婆。
毛尖:再说一个,最钦佩的第二个人是谁?不要说你儿子。
格非:说我老婆不完全开玩笑。
毛尖:你认为自己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娶了你老婆。
格非:你替我回答了。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意思?
毛尖:比如写了《登春台》最伟大。
格非:我觉得我最高的成就是做一个老师,这是我最有成就感的,过了很长时间,还会有学生跟我写信。
毛尖:你最喜欢的旅行是哪一次?
格非:1990年去西藏,待了两个半月。
毛尖:你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
格非:教师。
毛尖: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格非: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没有在他身边。
毛尖:你最看重朋友的什么特点?
格非:幽默。
毛尖:你最讨厌朋友什么特点?
格非:自以为是。
毛尖:你这一生中最爱的人或东西是什么?别说老婆了,最爱的东西是什么?
格非:我喜欢植物,从小喜欢植物,而且对植物很敏感。
毛尖:可以从《登春台》最后一章中看出来,养花成了格非老师最大的隐喻。
格非:世界上四种东西,植物、动物、人、神,我肯定选植物。
毛尖:你下辈子想做植物吗?
格非:未尝不可。
毛尖: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家庭一件事,那会是什么?
格非:为什么要改变?
毛尖:问卷没有为什么,如果可以改变你想改变什么?
格非:我觉得不需要改变。
毛尖:已经完美到这个地步了?
格非: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不需要改变。
毛尖:如果你能选择的话,你希望让什么重现?
格非:我所要的东西,我没有办法领悟它,只能被暗示出来,这种东西不是可见之物,所有可见之物都是有限的。
毛尖:你到现在为止,最快乐的一个瞬间是什么时候?
格非:生活中有很多快乐,有很多瞬间,这个瞬间是什么瞬间?没有任何心思,比如我给学生考完试,成绩登完了,我发走了,这时候突然觉得一个学期课上完了,所有工作放在一边,元旦刚到,春节没有到,我可能有两到三个礼拜是空的,心里没有任何事情,非常幸福。
毛尖:我大学时候格非老师是我们写作老师,那时候传说你们最后考卷收完不改,把考卷往地上一扔,第一张的卷子拿最高分,有这回事儿吗?
格非:我看到过毛尖老师在不知道哪个场合说到我的时候提了这个事情,我一直想,什么时候见到毛尖老师加以更正,据说是我们老一辈钱先生他们那代里的某一个教授干的。
毛尖:你觉得这是很好的还是?
格非:好,学生只要把作业完成就行了,有一个老师是真的,他人比较善良,他给学生打分从85分打起,85,下一个86,87,一直打到95分,再回过头打。学校又需要分数,怎么办,就闭着眼睛打。
毛尖:我下次也这么干。
格非:你很难判断89的分的人和90分的人真正差在什么地方,文学这个东西,很难判断,学生不能不考虑分数,我作为老师也是人,必须打出分数,总有高有低,你说一定不如比我高一分的人,不见得,给学生打成绩是很荒谬的事情。
扫码查看直播回放
运营团队
整理编辑 吕婉婷
海报设计 译林出版社
本文校对 柳宝庆
新京报书评周刊
隶属于新京报的文化领域垂直媒体,自2003年创刊以来,新京报书评周刊深耕于文化出版动态,向读者提供有关文学、社科、思想、历史、艺术、电影、教育、新知等多个领域的出版动态与学界动态,提供诸如专题报道、解释性报道、创作者深度访谈等深度文化内容。
责任编辑:
相关知识
格非对谈毛尖实录:写小说的人,把光照到暗面
直播预告 | 格非对谈毛尖:在人群与孤独之间
路内、毛尖、马伯庸对谈:我们把路小路留在了1990年代
“毛尖体”是怎么练成的?专访“影评界黄蓉”、华东师大教授毛尖|封面·人物
巫鸿、黄小峰对谈实录:“中国绘画到底是什么?”
郑小驴获“中篇小说奖·主奖”:如同黑暗中一束光,照亮前行之路|华语青年作家奖
作为对谈的写作:当作家面对作家
对谈|鸡毛蒜皮、家长里短,其实最见历史深意
格非《登春台》书写当代生活:“孤独”是一种更好的连接方式
祝勇出“著述集”展现个人写作史:写作是一生的事业|谈艺录
网址: 格非对谈毛尖实录:写小说的人,把光照到暗面 http://www.pyqsh.com/newsview60044.html
推荐社会生活
- 1一个人,也要好好生活 2073
- 2新疆美女哈妮克孜恋情揭晓,男 2064
- 3中华民国双旗开国纪念币一枚能 1836
- 4细读《金瓶梅词话》第35回之 1790
- 5李清照:两处相思同淋雪,此生 1253
- 6金莎的穿搭给人一种精致土的感 1155
- 7周杰伦晒和昆凌游玩照 同和小 1064
- 8据李子柒友人透露,李子柒已经 1051
- 9苏志燮宣传新片不忘撒狗粮,大 928
- 10自毁人生!池子再说无底线言论 916








